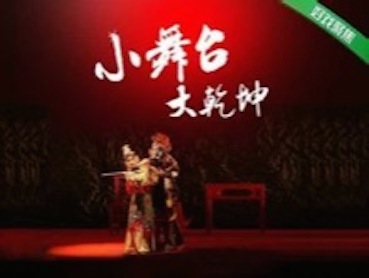
【热点回放】
中国戏曲与西方话剧同台 小剧场创新建立良性生态模式
2016年“北京故事”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日前在京收官,在之后举行的总结研讨会上,北京市文化局相关领导、业内专家学者和展演剧目创作者,针对国内小剧场戏剧创作、演出现状展开讨论,共商小剧场戏剧未来发展之路。
打造“大北京”的文化概念
本届展演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,共有来自全国的50余部作品报名,最终18部入围。展演分为“北京故事”与“小剧场戏曲”两大板块,其中,以戏剧、舞蹈为主的“北京故事”板块包含11部优秀作品,以各戏曲门类小剧场创新作品为主的“小剧场戏曲”板块共有7部优秀作品。在为期一个月的展演中,共有36场演出在北京12个剧场举行,观众逾万人。
据了解,自2012年第一届“北京故事”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举办,至今已是第五届。“北京故事”已成为北京标志性、品牌性的文化项目。
本届展演旨在打造“大北京”的文化概念,因而参展作品也第一次扩大到全国范围。本届展演共有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《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》等3个非北京地区剧目入围,均表现出不俗的票房和口碑。
小剧场戏曲成为重要部分
近年来,地方戏曲的传承与发展越发受到重视。其中,小剧场戏曲表演模式日趋成熟,并逐渐成为小剧场戏剧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本届展演加大了“小剧场戏曲”板块的剧目数量,鼓励传统戏曲院团积极创新,创作出与当代社会审美观、价值观更加契合的小剧场戏曲作品,吸引更多观众品味传统文化的新魅力。
老戏新编的梨园戏《御碑亭》和“90后”团队打造的粤剧《浮世三生梦》成为本届展演的亮点。除此之外,《明朝那点儿事——审头刺汤》、《断肠辞》、《望乡》、《三岔口2016》、《古城暗战》都在年轻观众中有着非常好的口碑。
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梧桐对《古城暗战》尤为赞赏。他认为,该剧是由六七种曲艺的曲种串联出来的舞台剧,更像一出曲艺剧。“这样一个主旋律题材用曲艺的形式来演绎,让人大开眼界,对曲艺而言,这个戏的价值实在太大了。”梧桐说。
对此,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、秘书长杨乾武谈道:“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,因为我们有两大戏剧母体——西方的话剧和中国的戏曲。这两大母体的融合是今后戏剧发展,特别是小剧场戏剧发展的方向。”
小剧场成为年轻人交友新平台
从少数戏剧先锋的实验田到今天话剧艺术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,小剧场戏剧不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,也逐渐发展成为年轻人交流、交友的新方式。
为充分了解广大观众对于本次展演的真实反馈,在展演的36场演出现场,主办方均进行了调查问卷。在“观看本剧原因”的调查中,“与朋友约会”成为重要原因之一,而观看小剧场演出的主流群体则是18岁至30岁的观众。
作为调查问卷的实施方,宽友(北京)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建城坦言,对于观看剧目的原因,除了口碑传播,如朋友圈发布信息外,“与朋友约会”这个答案令他意外。“我发现,因与朋友约会而选择观看的剧目,大都是都市题材,或是形式感很强,如《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》、《催眠》、《幸福年》、《YAO》、《二十四节气》等。”
《浮世三生梦》剧组代表则表示,作为在校生,他们非常珍惜“北京故事”这个平台。虽然,该剧在学校拿过奖,但少有机会在校外平台进行演出。“从学生作品的角度来讲,如果能有其他单位提供制作帮助,对我们的创作真的非常有利。”《浮世三生梦》剧组代表说。
建立良性小剧场生态模式
据展演调查显示,观众对于本届展演内容的满意度为91%,剧场观演环境满意度为86%,票价设置的满意度为88%。观众的高满意度离不开良性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。梧桐表示:“‘北京故事’这5届我都参与了,值得欣喜的是,这一届形成了良性的戏剧生态模式,这种模式是组织方、运营方、策划方共同配合的结果。”
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小剧场戏剧专业委员会主任傅维伯表示,良性的戏剧生态模式要靠“规矩”来维系。“小剧场戏剧的市场本身很小,所以需要我们的创作者、参与者形成合力,以制度和规矩为约束,共创小剧场戏剧更美好的未来。”
北京市文化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吕先富表示,作品只有多演才能立得住,“北京故事”为好作品提供了演出平台,希望今后能从这个平台中多出精品。
(以上来源:2016-09-29 中国文化报 )
2016“春雨工程”在西藏启动 实验剧·藏戏秦腔《图兰朵》首演
6日,实验剧·藏戏秦腔《图兰朵》在西藏自治区藏剧团藏戏艺术中心举行首演,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藏戏专家的一致好评。据了解,该剧是首部藏戏与秦腔相结合的剧目。
首次将藏戏与秦腔相结合
10月6日,由中国戏剧学院学生、西藏青年藏戏演员索朗曲珍执导,20名自治区藏剧团优秀演员和4名中国戏剧学院学生共同演绎的实验剧·藏戏秦腔《图兰朵》在自治区藏剧团藏戏艺术中心上演。该剧首次将藏戏与秦腔相结合,并入围北京市第三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节,也是藏戏第一次跨入小剧场。
《Turandot(图兰朵)》是由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贾科莫·普契尼根据童话剧改编的三幕歌剧,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传奇故事,主要讲述中国公主图兰朵与异域王子之间的故事,从图兰朵、鞑靼王子和柳儿三人间的爱恨情仇入手探讨人与爱情的关系,曾被改编成京剧、川剧、冰上舞蹈等艺术形式。
关于为何将藏戏与秦腔结合,总导演索朗曲珍解释,学习过各种不同剧种后,她发现黄土高原特有的唱腔秦腔与青藏高原的藏戏在唱腔上很相似。“所以我想将这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艺术结合,呈现出藏戏与秦腔的‘各美其美’,发现两者的‘美人之美’,探索两者‘美美与共’,力争成为具有雪域、黄土两大高原独有戏曲剧种元素的佳作。”索朗曲珍说,《图兰朵》是西藏扶持青年创作人才的项目之一,相信戏迷们将来会看到更多更有趣的戏剧形式。
获得观众专家一致好评
今年27岁的索朗曲珍是一名青年藏戏演员。12岁那年,索朗曲珍通过全区公招进入自治区藏剧团,在成都学习过3年的舞蹈,并在西藏大学艺术系藏戏表演班学习了3年。为了在藏戏方面有更好发展,参加工作后的索朗曲珍选择继续学习,于2013年考上中国戏曲学院导演专业,成为藏戏史上首批本科生。索朗曲珍参加过各种大型藏戏表演,如今,藏戏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。
实验剧·藏戏秦腔《图兰朵》是索朗曲珍在工作之余编排的,从排练到彩排只用了5天,在7天里完成所有准备工作。演出结束后,剧目获得了现场观众和藏戏专家的一致好评。“以前在台上觉得演员是最光鲜亮丽的,现在才发现,如果没有幕后工作人员将无法成就幕前的光鲜亮丽。”索朗曲珍说,“正是有了大家的努力,才有了如今剧目的成功上演。”
(以上来源:2016-10-11 西藏商报 )
走进小剧场,戏曲能否改变“陈词滥调”?
王侯将相,才子佳人,一桌二椅,陈词滥调,这或许是戏曲给很多观众的刻板印象;但如果舞台上,用小和尚和风尘女的爱情探讨人的纠结与欲望,用黑白剑客的斗争展现人性挣扎,演员身影在池水与天幕间交织,观众可以起身跟学基本身段,你会不会改变对戏曲的看法?
历时50多天的第二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日前在北京繁星戏剧村闭幕。京剧、昆曲、秦腔、豫剧、河北梆子等多剧种及混合形式的12个剧目,通过小剧场这种形式,吸引着更多年轻观众走近戏曲这一传统艺术。
主题创新:跳出“善恶评判”,深入“人性”“灵魂”
10年前,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曾说,中国的传统戏曲受儒家实践理性和实用主义影响,不管是讲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,传递的都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善恶评判;而西方戏剧则重于自我救赎的思考,因此有着对灵魂更深刻的关注甚至拷问。
而此次的艺术节上,部分剧目则跳出这一窠臼,将关注点伸向了人性和灵魂。
根据敦煌壁画故事改编的京昆剧《荼蘼花开》只有两个人物,全场只是小和尚和风尘女子两个人的“博弈”:为情所动破戒后,是选择儿女情长还是回归佛法无边?突遇的世俗之情能否战胜长久的信仰浸润?
“本剧以喜剧形式,涵藏悲剧意蕴,探讨现代人在理想与现实中的困难选择。”该剧导演、主演常秋月说。
有趣的是,脱胎于明代剧作家徐渭剧作的昆曲《四声猿·翠乡梦》与《荼蘼花开》故事极为相似,也都用梦境作结,但人物关系作了一次反转。编剧张静说,“剧作着力于探讨人与欲望之间的关系,用看似荒诞的故事,揭示‘心”即理的哲理。”
京剧《馒头山》改编自台湾剧作家纪蔚然独幕话剧《死角》,剧中行走江湖的白衣剑客意欲登临馒头山上的寺庙出家,却被神秘的黑衣人阻拦,盼望皈依佛祖可又心生波澜。导演徐春兰说,该剧着重表现人生、人性和自我内心善与恶的纠结、斗争与毁灭。
上海市文广局艺术处调研员方家骏指出,小剧场戏曲可以把大故事集中到小剖面,聚焦到一两个人物身上,挖掘更深层面的心理活动,更贴近现代人的视角。
而在中国评剧院编剧冯静看来,剧场空间的从大到小,也拉近了演出和观众的心理距离。“小剧场提供了一个机会,把人们不以为意的老戏拿来重新包装、打磨,赋予情感,和当今人们的感情接通起来。”
舞台创新:剧种融合,重视舞美,改变观演关系
自1982年林兆华导演的话剧《绝对信号》起,中国大陆开始将西方的小剧场概念引入戏剧,而1999年前后《马前泼水》的问世则标志着小剧场戏曲的滥觞,后来又出现了《玉簪记》《浮生六记》《碾玉观音》等代表作,如今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借助小剧场创新戏曲艺术。
本届艺术节中,《荼蘼花开》《馒头山》尝试将京剧和昆曲融合;《三岔口2015》融入话剧、河南曲剧、吉剧、武术、现代舞元素,演员跳进跳出的表演,台上台下的互动交流,使观演关系产生变化。
戏曲儿童剧《玩具星球奇遇记》采用儿歌化的台词风格,融入卡通化的生旦净丑,建构出一个玩具时空;小剧场的表演区与观众区相连,孩子们可以近距离地看剧中人物挥刀舞枪,甚至可以起身跟着学习京剧中的基本身段……
《馒头山》中,主人公一黑一白两套服装,皎洁的月光和斑驳的树影,制造出对比,烘托了人性中善与恶的较量,营造出别样的禅意。
同样着重在舞美上花了心思的还有《四声猿·翠乡梦》:台前有一汪池水,演员的身影在水面与幕布上交织。“我们在作品中试图探索戏曲到底需不需要舞美,如何与舞美结合,如何在当代剧场里呈现昆曲。”编剧张静说。
“小剧场最原始的动力、最吸引人的地方,就是创新,就应该做最前沿的东西。”本届艺术节艺术总监、京剧表演艺术家周龙认为,实验性、先锋性是小剧场的核心特质,能给戏曲发展提供更多的探索空间。
道阻且长:创新仍是前行动力
北京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已经走过两个年头,参演剧目的水准得到了认可,但是专家认为,小剧场戏曲的探索仍然刚刚起步,小剧场戏曲的前行动力,仍然在于利用小剧场的特点,进行创新。
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杨乾武指出,戏曲是注重传统、注重程式的艺术,改变起来较为困难。“有的剧目在表现形式、整体结构上创新了,但是把传统戏的内涵抽空了,传统的生活方式、人生经验、伦理道德都没有了,这是不行的。”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陶庆梅认为,小剧场戏曲走向成熟所需的时间要比小剧场话剧更长,“前几年市场可能不那么好,我们要耐得住寂寞。”
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指出:“大剧场表演与观众之间有相当的距离,表演要求夸张,动作幅度较大。到了小剧场,就要把表演收拢,变成非常细腻的心理和细节的刻画。”
“小剧场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它的特质、它独立的美学,能让年轻人产生共鸣,能激发创作者的热情,让他们自由发挥、探索、创新。”本届艺术节秘书长樊星说。
(以上来源:2016-01-24 新华社)
【数据分析】
小剧场只是其表层意思和物质形态,其深层内涵和实质是在精神内涵与表现手段方面进行探索创新,以更亲切的方式和更小的范围内的观众进行更私密的精神交流。当大剧场戏曲更多承担深沉历史题材创作的时候,小剧场戏曲更应探索未来出路。
长期以来,人们对于戏曲的发展莫衷一是。沮丧者有之,自恋者有之,随波逐流者亦有之。一段时间里,部分基层戏曲院团的处境并不让人乐观,而戏曲理论界在讨论其出路之时,也在“继承”与“创新”之间“举棋不定”。与其犹豫旁观,毋宁大胆实践,一些院团开始大胆启用、培养年轻演员,老艺术家尽心尽力“传帮带”,坚持出戏出人,目前看来已初步显出了良好的效果。日前的这一系列演出让人深深地感受到戏曲薪火延绵的温暖,更让人看到了戏曲发展的未来希望。
小剧场对戏曲内容有改变乃至决定作用。如何用好小剧场戏曲节这样的形式,有希望改变决定当代戏曲以及未来戏曲的内容。
小剧场戏剧在欧洲出现的时候,宗旨之一是反商业化,但是到了中国情况不同了,中国引进小剧场戏剧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继承了欧洲小剧场戏剧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实验性、先锋性,但是没有反商业性元素,因为当时无商可反。后来商业性日渐膨胀,又挤压了小剧场戏剧原本的思想和艺术上的先锋性。现在看来,小剧场戏曲也是更多地在艺术和思想层面寻求突破。其实戏曲是存活在一个三维立体空间里的,思想、艺术和市场,三者缺一不可,一定是在当中最好。
戏曲可以有尽量深刻的思想,但是表达不能过于深刻,否则就失去了大众艺术的特长。戏曲技艺可以追求繁杂,但是表现不能繁杂,否则成不了文学艺术。十多年以前的小剧场戏曲,过于片面追求思想和艺术,忽视了市场。
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年轻人缺少登台机会是许多院团尤其基层院团的普遍现象。当然,其中有很复杂的原因,比如戏曲整体处于市场低谷、院团处境困难、排戏“僧多粥少”等,但这确实造成了一些演员在嗓子、身段最好时未能得到足够的锻炼,而到人生阅历、艺术理解成熟之际又错过了最好的年华。让人欣慰的是,如今良好的政策环境、积极创新的院团举措、老一辈艺术家尽心尽力的“传帮带”,使年轻戏曲人才迎来了春天。
或许,年轻演员亮相本身包含着他们自然成长、接续薪火的历时过程,但从近些年各地戏曲院团的发展看,最大的亮点无疑是“传帮带”之外又增添了一个“推”字。推新人,推新剧目,推新的创制模式,等等。小剧场本身是现代性的标志,它的气质、品质就是定位在现代性上。艺术作品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塑造新的形象,一部戏好不好,就在于它塑造了什么样的形象。改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使我们戏曲走向困境的最重要的因素,应该走一条改本之路,在精神气质上,在文本的本体上做一番彻底的改变。
|